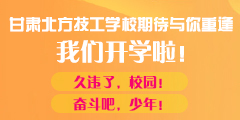五颜六色的花盆吊挂在冷冰冰的通气管道上,绿色从盆中溢了出来。北京一所学校的这间教室是她最新的一块阵地。
已经是期末前最后一天的课了,这里看起来更像是在迎接一场盛大的狂欢。班主任李虹霞就是盛会的主角。
讲台上没有老师,一排装满了书的柜子站立在那里,随手一抽,就能找到一本《丁丁历险记》。后墙的书柜前,还铺上了看起来像草地一样的柔软垫子。
一排排课桌,被打乱成一个个小组,四个小朋友对面而坐。他们不需要挺直腰板手背后,当欢快的音乐在语文课上响起,还有宽敞的空间让他们身体可以摇摆。
为了让刚入学的孩子尽快识字,班里三十多个学生的姓氏,被她编成了新的“百家姓”,朗朗上口;繁复的字词附身在一张张鲜艳的纸片上,贴在教室空出来的地方,孩子玩耍的时候可以顺便和它们认识;李虹霞给孩子朗读课文,在冬天的教室里,富有节奏的声音像皮球一样一弹一跳。
她写过一本书,叫《创造一间幸福教室》,这本2013年8月出版的书,一年之内已经印刷了5次。
从90年代就开始做教育的李虹霞,曾经亲眼见识过恐惧的力量。师专毕业以后,李虹霞在当地的职业中专和技校任教,她听的最多的就是学生讲过去老师的坏话——罚站、写检查、开大会批……
让学生安静下来听课,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“大多数对学习知识并不感兴趣,连武侠小说都看不了”。生日时她收到技校学生送的一个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礼盒,卡片上的6个字错了两个。
彼时,儿子刚好也快到上小学的年纪,于是她决定到小学去,“看看教育的源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
教育师专学中学教育的她,并没有小学教育的背景。李虹霞本来以为,“教育就是按照规律来”,但是到了小学,她发现把事情想简单了,“看到了很多违背规律的地方”。
她见过,一年级刚入学的小女孩因为练习拼音手指上磨出一层老茧,也曾见过,教室里学生太多所有课本习题册必须装进厚厚的书包,卡进孩子后背和椅背之间的有限空间里,挤得人动弹不得。
“我们都说以孩子为中心,但我们做过什么尊重孩子的事情?”在地下室安静的咖啡馆里,今年46岁的李虹霞不自觉提高了嗓门,“学生们来学校时低着头小心翼翼说‘老师好’的时候,和放学时挥着手特别高兴地说‘老师再见’的时候,根本就不像一个人!”
这样的经历李虹霞并不陌生。她小学成绩一直不好。“不知道把铅笔削尖了再写,写出来的字永远是黑乎乎一团。”发考试成绩的时候,她只能把可怜的分数赶紧藏进抽屉。
“我们都知道孩子的起步要缓慢,要轻松。”李虹霞说,战胜恐惧的法宝其实很简单。
孩子害怕学拼音,她就把包含了字母的儿歌谱上曲子,唱给他们听;他们不喜欢写作文,她就鼓励他们不要一本正经地用作文本来写,而是在小纸条上一段一段地写给她。
在一次测试中,一个小姑娘面对题目哭了整整一节课,最后什么都没有写。李虹霞偷偷做了一个决定,把小女孩儿的试卷抽走,没有让任何老师看。
后来,李虹霞把小女孩儿不会的字做成一堆红红绿绿的卡片,让家长帮助她每天晚上学习。当孩子家长在微信上发来小女孩儿晚上练习写字的图片,她总是回复“你是我见过最认真的孩子”。
她总是善于把让人讨厌的任务变成游戏一样的闯关,写字差的小朋友哪怕只有“最后三个字写得漂亮”,她也会激动得捧着孩子的手说“你的手醒了”。一组关于大灰狼的课文让孩子厌烦,她就抛出诱饵,“我们认识一个字就是打大灰狼一下”。当课文读到大灰狼《葬身荒山》,全班都兴奋地喊“大灰狼终于死了”,干脆站起来,跳起来。
面对孩子们的恐惧,她还曾取得过更大的胜利。在山东省潍坊市北海双语学校,她同时带着来自不同年级的两个班级,后来都争取到了不参加平常考试,只在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参加统一考试的特权。
其实在刚刚进入小学的时候,李虹霞也属于善于考试的老师。她记得,学生每得一个百分,奖励老师一百元。在激励下,她总是拿很多奖金。有时候她的班级平均分比其他班级高十几分。
当她拿着考试成绩去向校长申请免考时,校长不解,“你分数那么高,为什么怕考试?”
“如果有考试,我就会盯着考试去准备,这样我的焦虑就会转嫁到孩子身上。”李虹霞说,当教师多年,她经常看见考试后,老师机械地把学生所有的成绩变成一个个单调的数字,填在表格中。
没有了考试,李虹霞果然在班级里有了更大的空间。
一个从二年级留级下来的学生,成绩差到年级闻名。通过抓阄把他纳入自己的班级后,李虹霞觉得他“过得很快乐”。这个爱踢足球的男孩,在和班级队一起赢得学校足球比赛冠军后,李虹霞还让他做了国旗下的讲话。
有轻度自闭症倾向的小秦,上课从来都不能集中注意力,老师叫到名字,他就慌乱地翻书,却连页码也找不到。她就挑选他写的博客文章念给全班同学听,虽然他写的内容,大多都是和妈妈逛街的路上,踢了一块小石子之类琐碎事儿。
小学的女生总是比男生乖巧,更容易被老师选为班级委员,她认为“班委的强权严重助长了女生的强大”,干脆取消班委。
看到其他老师还在课堂上用传统的教学方法,连绘画课都要先讲半节课,让爱画画的孩子感觉意犹未尽,她就争取由她一人来讲语文、绘画、音乐、甚至科学。
“这样孩子的学习不至于被分成一块一块的,老师也有更大的自主权。”李虹霞说。
在她讲的绘画课上,孩子不用按照要求画出花花草草,可以任意在画纸上涂抹,甚至于让长颈鹿的脖子绕几个弯,最后变得比教室高,比云彩高。这个语文老师趁机告诉孩子,这就叫想象,就像文学中可以把气势磅礴的乌蒙山想象成小小的泥丸,也可以把人的心想象成针尖。
她告诉孩子练好字是“打造自己的第二张脸”,也为孩子买了葫芦丝,教他们合唱。有人见过这个语文老师指挥合唱时的样子,“笨拙却努力”。
曾经参观过山东潍坊“幸福教室”的人说,那是一个比正常教室都大的屋子,李虹霞特意在屋里搭起一个大大的舞台。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表演。
这是李虹霞最在意的空间。为了打造幸福教室,她曾经专门去上了拓展班,“激发内心力量那种”,但实际的困难还是超出她的想象。
不考试的请求,获得了校长的认可,可是这个班缺少的练习册和测验试卷,让应付教育检查的同事担忧。而且虽然说幸福教室可以不参加平常的测验,但是必须面对小学毕业时的那次考试。
“应试教育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,一时很难扭转过来,”这个一直强调幸福的老师说,“如果分数不能过硬,在学校不能立足的。”
在更多的时候,她只能在妥协和激进中间摇摆前进。她会把考试的内容,分成一个个小的知识点,让学生早早就开始练习,或是由孩子自己设计试卷,把考试弄得五彩缤纷;同学们也经常见到她和校长争得面红耳赤。
“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,每次看到教室里的孩子痛苦,她就忍不住。”一位朋友评价她。
李虹霞说,自己最喜欢的一篇短文,是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一篇小短文《我交给你一个孩子》。
“学校啊,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,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?今天清晨,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聪慧的小男孩,多年以后,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少年?”
6年之后,她到底能还回怎样一个少年?工作从山东来到北京,她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到焦虑。
一段时间后,她发现那位在考场上一直哭的小女孩儿再也不哭了,上课经常举手。在一次民主选举中,她还被评为“爱心大使”。但是提到那位山东潍坊的小秦,李虹霞却有些高兴不起来。
有一次她回到山东,发现小秦已经被老师调到了最后一排。而落在老师视线之外的小秦,也经常被人欺负,“衣服、床单都被撕烂了”。
曾经,她一直把小秦调到了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坐下,还挑时间把小秦支出教室,然后告诉其他同学欺负他“只能显得自己无能”。可是现在,离开山东的她不能再以班主任的身份回到那里,只能给同学们写一封信。
“我最关心的秦,现在到底怎么样了?”在信中,她写道。
在北京,总是把语文课堂搞得丰富多彩的她,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。下课的提示音总是混进她朗读的声音里,她想要把课堂延长五分钟,在外面焦急等待的家长都会委婉地催促她,“老师,下次能不能准时一点?否则孩子要赶不上接下来的补习班了。”
她想布置一些课外书目,总会有同学告诉她没有时间,她这才知道,孩子们的补习班,最多能每天都有,有的小朋友,从小学一年级已经开始报班为升入北京著名的初中做准备。
撤掉讲台,把排列整齐的课桌打散,让学生们上课可以面对面交流。开明的校长表扬她“做得好”。
如今的幸福教室,就在楼梯拐角的地方。这里是整个楼层空间比较小的一个教室。
延伸阅读:
- ·教室怎能不见光(2015-11-30)
- ·家长自愿为教室购置空气净化器,不妥在哪里?(2015-12-28)
- ·教室变“圆”了又何妨?(2016-09-21)
- ·轨道交通运输学校:教室进实训室 上岗学技能(2018-05-02)
- ·交通部谈中小学生溺水事件:普及安全知识很必要(2015-04-17)

 护理专业
护理专业  多媒体制作
多媒体制作  铁路工程测量
铁路工程测量 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
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 铁道类专业专题
铁道类专业专题  幼儿教育专业
幼儿教育专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