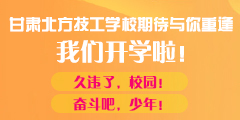|
西南联大校门 引言: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块普通的石碑,静静立于校园一隅。 石碑正面,记下一所仅仅8年的大学的历史。碑阴,刻着832个名字。 这块石碑,名叫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。832个名字背后,是该校抗战以来从军的832名学生。 石碑立于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。另外3块内容一样的石碑,分立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。每逢“五四”这样的节日,碑前总会铺上束束鲜花。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不久,平津陷落。8月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。1938年,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1946年抗战胜利后,联大“胜利关闭”,三校各自北归复校。 风雨如晦。在时空的纪年中,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,但对西南联大,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。 在战争风云之下,民族存亡之际,它临时拼凑而成,条件恶劣,衣食不充,加之日寇轰炸,师生要冒着生命危险上课。但他们赓续文化,弦歌不辍,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。 陈寅恪、冯友兰、陈岱孙、闻一多、华罗庚、费孝通、吴宓、陈省身、曾昭抡、杨振宁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。在这里,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…… 如今,70多年过去,渐行渐远的西南联大已然成为传奇。那么,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?让我们因循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动人的故事,还原这段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可磨灭的时光。 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夏日的清华园,秀美静谧。 虽已放暑假,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,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,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。学校一、二、三年级的学生,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。 深夜,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,打破了校园的平静。 这一天,是1937年7月7日。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,借口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,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。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,又炮轰宛平城,中国军队奋起抗战,震惊中外的“七七事变”爆发。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,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。 日寇占领北平后,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,图书、仪器、标本被洗劫一空;北京大学红楼,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。 7月29日,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,校园被焚毁。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:“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,这是一个反日基地。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。” 南开的创办者、校长张伯苓,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,静默地坐了一会儿,大义凛然地说:“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,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。” 这三校中,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,前身是京师大学堂,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。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,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,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。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最优秀的私立大学。 随着清华、北大被占领,南开化为残垣,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。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,决定将北大、清华和南开合并,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。 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的南迁,并非当时特有现象。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、华东,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,至1941年初,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,有77所南迁。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
从左至右: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 1937年8月28日,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,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,勘定校址,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、经费分配等事宜。 此时,从北平、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,通过各种途径,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。这些师生中,有的是徒步到长沙,有的甚至沿路乞讨,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,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、资料,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。 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,其中清华631人,北大342人,南开147人,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,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。 在各方努力下,1937年11月1日,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。这一天,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;也是这一天,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,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。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,终于在湘江之滨、岳麓山下,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,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。此时,拥挤的教室,摇晃的危楼,已经没有人再计较。 如前所述,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、师生都各有特质,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“整合”在一起,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。 蒋梦麟回忆说:“在困难时期,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。而在战乱中的年代,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,无异难上加难。” 由于种种原因,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——一位低调而高效的管理者。他主持秘书、教务和总务工作,负责校舍建设,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。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、法商学院、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。同时,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、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。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。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。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,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。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,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,除土木工程系外,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;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;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。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,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。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%左右,勉力能维持生计。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,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,几乎一贫如洗。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,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。 由于缺乏教室,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。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,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,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。学生缺少课本,只能依赖上课听讲,而老师也缺乏资料,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。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,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,这一时期,汤用彤完成了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一卷,金岳霖《论道》问世,冯友兰的《新理学》也已经杀青。 |



 护理专业
护理专业  多媒体制作
多媒体制作  铁路工程测量
铁路工程测量 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
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 铁道类专业专题
铁道类专业专题  幼儿教育专业
幼儿教育专业